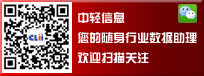凡登伯格 | 逻辑、人工智能与文化
几十年来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这一研究采用的假设是,人类做的一切事情都是运用规则和算法的结果。他假定了什么可以被称为信息人,而且还试图将文化和语言世界带入到逻辑世界中去。但现在几乎人人都看到了这项研究并没能实现它的原始目标。休伯特·德雷福斯的理论准确地预测了为什么人工智能没能在任何一个最初假设上都获得成功。该理论认为,由于计算机不是嵌入到世界中的,所以它们就不能对世界进行“经验”,更谈不上在其中有理智地“生活”了。这里我主要讲几个现象。人类嵌入到这个世界上含有两个维度——身体维度和形象维度。这两个维度在大脑—思维中合二为一, 而且同自然世界和文化—历史世界共同向前发展。当几乎放弃了对一般的人工智能的找寻,转而开始支持用专家系统创建一种高度有限的智能的时候,达孚兄弟就推出了我们前面讨论过的人类技能获得的五阶段模型,并向大家展示没有一台机器能够走到第三阶段以上,这也就表明理性图示是有极限的。准确地说,其实我之前已经提到了,第三阶段以上是元意识知识发挥决定作用的地方。而元意识知识是由身体上、形象上都同时嵌入到世界中才能获得的。
此外,人工智能还面临着其他一些限制。无论什么时候,只要“纯”逻辑和数学被植入机器中或是人脑中,就会出现一些身体上和世俗中的限制,然后就会频繁地引发算术的 激增。由于这种植入,任何机器或人脑都不可能完全具备理性,因为它们没法处理像无穷级数或是无穷数位串之类的问题。事实上倒是能够利用这些限制让计算器产生出一些绝对无意义的东西来。由于所有这些系统都是由人建造出来,并由人操控和使用的,所以植入引起的限制总是发生。比如说,有些验算过程非常长,可能需要超过一生的时间才能将它们写下来或是读完。假设有一位信息人要决定是在七点起床还是七点半起床,如果他七点起床了,就能先做个丰盛的早餐,然后给朋友打个电话,再步行去工作等等。如果他七点半起床了,多睡的那半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就只够他去上班了。这两种可能性无论出现哪种,都会影响到后面发生的事,进而还会对其他事产生影响,所以一切都需要进行计算才能保证生活的每一瞬间都可以获得最大的效用。如果要试着通过常规的人工智能方法来模拟这一切的话,立马就会引发组合爆炸。

著名旗手柯洁在与人工智能机器人“阿尔法围棋(Alpha Go)”下围棋。[图源:搜狐]
在用计算机模拟常识的问题上也遭遇了同样的植入限制。假设某个人所有的经验都能存储在一个计算机存储器里。那么现在的任务就是:给这台计算机编程,让它能就一些简单的日常生活问题做出回答,或者能对一个情形给出解释。如果一位出纳员在银行中发出尖叫声时,我们在面对这样的情形时是不会遇到组合爆炸的问题的,因为该情形的每一个方面都有一个意义和价值,而根据这些不同的意义和价值我们能够指出某一方面在同对该情形的解释上存有怎样潜在的联系。于是我们立刻就能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状况。可是当前的计算机并没有意义和价值,所以它们就得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检查一遍:出纳员尖叫是因为有辆红色车开过了?还是某个母亲抱着孩子走进来了?还是一位客户说早安?或者这位客户穿了身蓝西服?还是其他的什么呢?这种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就算把计算机的结构改建在神经网络上能将其中一些这样的限制消除掉,但人类对于自我的意识和对于世界的意识问题始终是存在的。
纯逻辑系统和数学系统本身也有局限性。1931年哥德尔证明复杂的演绎系统是不完备的,它们具有的内在一致性是无法得到证实的。之后,图灵又说明就算图灵机能计算无限多的步骤,因此能够一直不停地将某个证明完成下去,但是有些问题还是没法解决的。因为很显然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用数学来表达的。在数学之外还存在着一个非逻辑的领域,不论什么时候,只要当代的各种生活方式需要借助数学来改善什么东西的时候,就会把非逻辑领域剔除出去。还有人论证说纯数学其实并不存在,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的话,它就不能完全从经验和文化中独立出来。经验和文化的领域似乎是非数学的,也就是说,这个领域是不能被包含在数学领域之内的。

艾伦·麦席森·图灵(AlanMathison Turing,1912-1954),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被称为计算机科学之父,人工智能之父。
有一段时间,人们对唯理论的世俗信仰从未受到过质疑,唯理论连篇累牍地对文化进行谩骂,称文化是主观的、迷信的、宗教的,总之一句话,文化让科学和技术的时代蒙羞;现在这段时期好像行将消失了。唯理论没有意识到,其实文化取得的诸多成就可能是人类最重要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创造物了。毫无疑问,文化像其他任何人类创造物一样并不是无所不能,它有它自己的局限。当这些局限公之于众的时候,我们必须学会将它们识别出来,并接受它们,除非我们绝对有把握能够创造出另一种替代品来理解这个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我想要向大家证明无论是科学也好,还是技术也好,都不能提供这样的替代品,因为人类仍旧得依赖文化进行初级社会化,然后通过这个初级社会化把那些去形象化了的当代文化所能传达出来的所剩无几的意义、方向和目的教给孩子们和年轻的人们。
有些观察家推测我们很快就会为人类存在找到另一种基础。这本是寻找永恒生命的继续,只是这次披上了世俗的外衣。这方面的争论似乎等于说是相信随着信息人的到来,人类生活很快就会永恒。基因组计划应该是把生命的代码(DNA)还原成信息,供我们出于各种幻想进行存储、操控甚至复活成新的生命。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些研究者们仍然寄希望于能够把所有人类经验和文化都还原成信息。到那个时候,我们的身体和灵魂将全部被还原成信息的形式,而这将使它们在计算机、互联网以及其他未来的信息系统中永远“存在”下去。其实,这一切的信仰都是因为没能正确地认识技术与文化,也没能正确地理解技术和文化给人类生活带来的影响。简单地说,由于技术对人的改变远比人对技术的改变多,所以人类是在用技术的形象重造自身。现在已经不是完善计算机和机器人、让它们更像人类的问题了,而是人类变得越来越像机器人和计算机的问题了。

图为1982年上映的电影《电子世界争霸战/Tron》的剧照。电影主要讲述了由程序员设计的主控程序MCP 拥有自主意识后愈发不听人类控制,并企图控制世界。所以不得不被摧毁,从而恢复世界秩序。
技术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日渐呈现出一些显而易见的局限来。环境危机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我们的自然公地有多么的重要,于是,过去人们制作的那些效率低下的实体,还有被我们全部摧毁了的那些关系,现在都开始勾起了大家的思念。不仅如此,它还让我们认识到生物圈曾经具有多么令人叹为观止的适应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归咎于一切此物都是在与一切彼物的关联中演绎,结果每一种生命形式都能为其他所有的生命形式提供支持。同样的道理,传统社会还创造了社会生态,这些社会生态对于那些在精神上危及人类生活的东西也表现出了高度的适应性,它们对某种未知的实在施加控制,从而让它有益于人类生活。但现在在技术的帮助下,我们正用一种全新的联系将这种联系取而代之。这两种联系本都有许多长处和短处,但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技术联系并不是十分的有益于人类生活。结果,文化的角色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被当成是想当然的,同时也不能再认为文化发挥作用的领域一直是外在于人类意识,仅仅是在大脑一思维的元意识维度之中。
先是由于工业化带来的压力,之后又是由于技术合理性带来的压力,导致文化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开始出现衰退,之后不久社会科学领域就发展起了“文化”的概念,这一切并非仅仅是偶然。但正是这一发展态势日渐吸引了科学的目光,于是出现了当前对文化在人类生活中扮演的作用的理解。于是此时我们可以说,其实我们不仅破坏了自然公地,也将自身的形象公地一起破坏了,也就是同时危害了我们来自天上和人间的生命支持。我还要继续对我所宣称的“技术和文化之间是寄生关系”加以说明。如果当前人类的演化和调整已经日渐对个体和集体人类生活的非逻辑和非技术方面构成限制与制约,那我们就是在给自身造成不可估量的伤害;如果生活与量化、规则、算术、逻辑和神经网络无关,那我们就是在一步步地将迄今为止我们称其为人的东西破坏殆尽。人类生活的品质是非逻辑、非技术的,因此在当代世界无足轻重,但它到头来其实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曾如此成功地推进了历史的形成。可持续性不再仅仅是一个关乎我们同生物圈关系的问题了,它同时也是一件与文化和形象化有关的事。
相关新闻
版权声明
1、凡本网注明“来源:中国轻工业网” 的作品,版权均属于中国轻工业网,未经本网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它方式使用。已经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注明“来源:中国轻工业网”。违反上述声明者,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2、凡本网注明 “来源:XXX(非中国轻工业网)” 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信息之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3、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同本网联系的,请于转载之日起30日内进行。